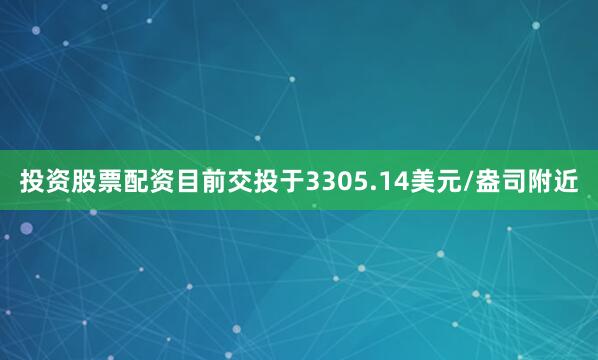图片
著名物理学家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,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103岁,从此20世纪的理论物理合上了它的最后一页。在量子场论、粒子物理乃至现代宇宙学中,几乎每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上,都能看到他的思想痕迹。
“对称不是完美的终点,而是自然的语言;
破缺不是混乱的开始,而是创造的起点。”
图片
01宇称不守恒:打破对称的世界宇称(Parity) 是物理学中描述“镜像对称性”的一种量。就像我们在镜子前举起右手,镜像中的你举起的是左手—动作看起来反了。如果一个物理规律在“真实世界”和“镜像世界”中表现完全相同,我们就说:这个规律“具有宇称对称性”,或者说“宇称守恒(Parity is conserved)”。
此前,科学家普遍认为,物理定律在“左手世界”和“右手世界”中应当完全相同。直到1956年,杨振宁与同事李政道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设想:自然界中的某些力,并不遵守镜像对称。他们特别怀疑的是弱相互作用(Weak Interaction)—也就是放射性衰变中控制β衰变的那种力。
几个月后,吴健雄在低温下用钴-60 原子核做了一个极为精密的实验验证了这一假设。这个实验发现电子更容易向与自旋方向相反的一侧射出,自然界偏向了一边—就像宇宙“更喜欢左手”。也就是说弱相互作用中,粒子表现出“左手性(Left-handedness)”,这个就结果震惊了世界。
1957年,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此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科学舞台上获得如此高度的认可。更重要的是,这一发现打破了人类长期以来对“绝对对称”的信仰,让我们重新认识到:宇宙的秩序,恰恰诞生于破缺之中。
图片
02规范场理论:力的语言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,杨振宁并没有停下科研的脚步。他继续关注着一个物理界的终极问题—自然界的相互作用(即四种基本力)是否有统一的描述方式。他与美国物理学家米尔斯(Robert Mills)合作,在1954年提出了后来被称为杨-米尔斯规范场理论(Yang–Mills Gauge Theory)。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:“力”是由“对称性”所产生的场。这个理论后来成为整个粒子物理标准模型(Standard Model)的核心框架。
20世纪,人们发现微观世界的“力”并非是物体之间直接作用。在量子场论(Quantum Field Theory)中,我们知道:力其实是由“粒子之间交换虚粒子”实现的。杨振宁和米尔斯提出自然界的相互作用,其实都来源于“对称性(symmetry)”,这种对称性即规范对称性(Gauge Symmetry)就是自然界四种基本力的本质来源。
当一个系统具有某种对称性时,数学上必须引入一个“补偿场”来保持对称性成立,这个“补偿场”就是“规范场(Gauge Field)”。而这个场,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“力”。四种基本力中的其中三种:电磁力、强相互作用力、弱相互作用力都可以用杨–米尔斯框架来描述,我们可以把“规范对称性”想象成一群人打伞走路:
电磁力是每个人都拿一样的伞(U(1)对称性)
强相互作用是每个人的伞颜色不同,但他们还会互相交换伞(非阿贝尔SU(3)对称性)
弱相互作用则是伞柄会弯曲、变化(SU(2)对称性)
保持伞的颜色和角度一致需要额外的规则,而这些规则就是“规范场”,也就是“力”。
图片
03思想与科学的传承杨振宁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,也是一位极具哲思的思想者。他常说,物理学最伟大的特征是“追求简单中的深刻”。无论是宇称破坏的惊人发现,还是规范场的抽象构想,都源自他对“自然之美”的敏锐感知。
在世界物理学的舞台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后,杨振宁选择了回到中国。1990年代末,他受邀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,长期在北京生活与工作。他希望将自己在国际前沿的科学思想与研究方式带回祖国,让更多年轻人能在本土接触到世界一流的物理理念。
在清华的课堂上,他常常不用复杂的方程,而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,用最简单的语言讲述自然规律的深意。他强调“物理不是公式的堆积,而是思想的训练”。他也常提醒学生:“科学不是模仿,而是发现。”
除了教学,他还推动了清华与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的交流,他建立了青年学者计划,支持中国学生赴海外深造并回国发展。在他认为,一个国家的科学力量,不只是实验室的设备,更是思考方式的成熟与文化的延续。他曾说“我一生最大的贡献,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不如人的心理。”
图片
END撰稿 | Harry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伍伍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